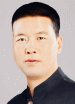0571-288834323
安全感在今天是智慧层级的东西,也是一种需要通过自我有意识地构建生活、调节自身的环境参数,才能换来的局部系统秩序。
从结构的视角来说,安全感也是一种冗余设计,它衡量的是你的心理系统在遭遇冲击时,有多少可以位移但不会断裂的空间。
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被某几个“安全支点”支撑起来的,它就像是心理上的承重墙,只要这些支点都在正常运作,人大概率会处在一种稳定和掌控感中。
安全支点的意义在于有效承重,所谓有效承重就是即便它遭受晃动,甚至断裂,却依然能够在整体上维持一种可复原的稳固。
一个人的安全感不能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建立在唯一对象之上,无论你依赖的东西是什么,那个东西也没有可能在绝对意义上确保自身的永久延续。只要它是单一的,无论它当下看起来多么稳固,它必然都经受不住一次真正的冲击。
人在什么样的心理水平,就会看见和感受到什么,就会朝向什么。
没人能在完全的easy mode中获得乐趣,人之所以乐于接受挑战,是为了获得力量验证,是为了在失衡和失败的边缘不断触摸那份可控感。
人的自我潜能需要有一个真正与之匹配的激发对象和进步参照,有时候你我都需要用困难来定义自己存在的量级。
我们总是会根据自身的心理效能水平,去选择能验证这个水平的自我的事情,并以此获得高级的胜任体验。用高阶版本的自我去做这个版本才能做到的事情,是人类成就动机和意义动机的最直接来源途径。
人很多时候的痛苦信念恰恰是被那些摇摇欲坠的防御机制所维系的,那是一种总是能够在低水平中复活,却又无法孕育出生机和活力的维生架构。
崩塌的意义在于它强制性地完成了你迟迟不愿进行的心理清算。它清除了所有虚假的繁荣,让你看清自己仅剩的、无法被剥夺的资产是什么,可以彻底舍弃的东西又是什么。
有时候覆灭好过于僵化的持久,但却不需要刻意去追寻,因为人不可能在自毁中重生,却能够在幸存中超越。
相关动态
#感情那些事# 4355546个回答
#人际关系# 1969575个回答
#压力太大怎么办# 1287545个回答
#我需要心理咨询吗# 1102569个回答
#职场二三事# 424696个回答
#个人成长# 6420560个回答
#抑郁求助# 396244个回答
#焦虑怎么办# 751035个回答
#心理咨询# 1729549个回答
#一句话描述你现在的心情# 1565071个回答